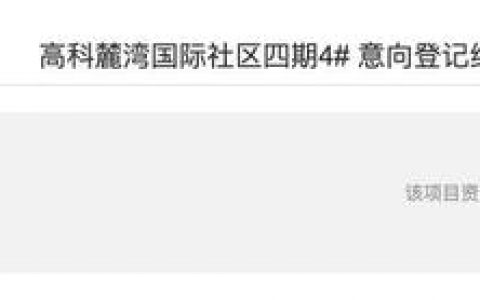一、引言中华文明的大师们
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,虽然其间存在断层,但是从不曾中断,顺势也好,逆流也好,文明的大潮依然滚滚向前,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。
不过,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,客观地讲,是因着不同历史时期站在文明巅峰的、具备顶级学问的个人支撑下来的。其中的一些人顺应了历史的进程,注定是成功的;另一些人则一意孤行,走向了失败。
纵观中华文明上、下五千年,动荡多,但是变革少。而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,战争还没有结束,国民党退守台湾,让大陆和台湾只能隔海相望,却无法触及彼此。
蒋介石的失败于是也成为了一些“大师们”失败。他们或出于无奈,或出于信仰、或者只是为了一份清净和自由,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。

这些“大师们”留在自己的位置上,或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,却成为了政治的筹码,或终其一生自由洒脱,却客死他乡,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依然是那个回不去的家乡……
二、傅斯年的独醉和独醒
1945年8月15日下午,傅斯年喝醉了。他独自一个人在家中笑着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笑什么,有那么多幸事值得笑,叫他怎么能不笑呢?是二战结束,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吗?不是,这件事只是其中之一。他笑,是因为终于可以不再忍耐,他笑,是因为中国依然挺立。战争结束了。
然而此时,喝醉的傅斯年并没有想到战争期间的苦和痛,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反而是战争期间的欢乐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,难道战争中也有欢乐吗?

他隐约听见窗外有人们的喊声和歌声。他想道,大家现在一定都跑到大街上去了。这想法又让他笑了起来。他抓起桌上的酒瓶,拿起拐杖,出了门。
还是夏天好,这是进入傅斯年脑中的第一个想法,还是夏天好。日寇占领沈阳是在九月,日寇占领北平是在七月。现在是八月,正好在两个月份之间——他又笑了。
他笑自己,到底是一个搞学问的,月份又有什么关系呢?他摘下礼帽——他不记得自己在家里也戴着这顶帽子——放到拐杖上,一只手高高举起,另一只手抓着半瓶酒,在大街上跳起舞来。随后,他又唱起歌来。
唱着唱着,泪水就流了下来。

中国还在这里,就在他的脚下,他深爱的中国,他深爱的北平赢得了战争。
当傅斯年在北京的大街上“跳着舞”、“唱着歌”时,他不会想到仅仅四年之后,自己就会离开他深爱的北京和北京大学。
北京大学也是傅斯年的母校。在北大,他师从陈独秀和李大钊,接受了古典文学和历史学的教育。他在古典文学中看到了永恒的死亡,又在历史中看到了短暂的生命。
比起历史,傅斯年更喜欢文学,他知道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命数,但凡世间的存在最终都会化为乌有。只不过,二战胜利的消息一时间让他迷乱了,让他幸福了。
1945年8月15日,日落之后,傅斯年才独自回到家中。此时的夜空下依然有人在庆祝,烟火照亮了地平线。正是这烟火惊醒了傅斯年——这火焰多么像战争时的炮火啊!

傅斯年低下头,盯着自己手里的酒瓶,就连酒瓶上也映上了夜空中的烟火。他感到手心一阵灼痛,放了手。于是,那酒瓶就掉落在地上,摔碎了。酒洒了一地,依然映着夜空中的烟火。傅斯年丢下庆祝的人群,离开了。
如今,身在台湾大学,傅斯年想起1945年8月15日的那个下午,感觉一切都是梦幻。对于已经五十四岁的傅斯年来说,只有学问才是真的——不,从来学问才是真的。
他立志要将台湾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学府,这就是他一生所追求的。也因此,他不愿意加入任何政党。他不理解为什么胡适先生选择了投身政界,他对此颇为怨恨。如今的胡适既不在大陆,也不在台湾,他追求的是什么呢?难道只是那仿佛转瞬即逝的烟火吗?

这是傅斯年来到台湾的第二年。此时的傅斯年当然不会知道,这一年会成为他生命的最后一年。他计划好了那么多事情,那些曾打算奉献给北京大学的一切理想,如今都将奉献给台湾大学。然而,等待他的却依然是残酷的命运。他先失去了大陆,现在,又将失去台湾。
或许,人在将死前真的会有某种预感,只不过没有人知道那就是“将死的信号”,而对于傅斯年来说,这“将死的信号”就是对五年前那个下午喝醉的回忆。
1950年12月20日下午,傅斯年参加了台湾省议会。他从来不想参加这些政客的游戏,但作为台湾大学的校长,是有这份责任的。
他做了发言,然后接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质询。傅斯年压着火,回答那些对教育一无所知的政客们的可笑问题。

时值隆冬,虽然是在南方,但天黑得依然很快。质询结束了。傅斯年起身走向自己的位置——那里才是我应该坐的地方,他心想,他突然感到太阳穴被电击了一下。
他看向窗外的夜空,心想,现在的北京大概也是晚上吧,多么可笑啊。他栽倒在那张座位前,再也没有想起什么。就这样,他死了。
三、孔德成的圣和凡
傅斯年——这位“五四运动”和“新文化”的旗手同样不会想到的是,仅仅在他过世的四年后,孔德成成为了台湾大学的中文系教授。作为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和中国的最后一代衍圣公,孔德成也用自己的一生相伴着孔家的兴与衰。

孔德成出生于1920年2月23日。这一年是中国有史以来“春节”最晚的一年。这一年的1月,《凡尔赛和约》生效,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尘埃落定,这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。这一年的2月,德国纳碎党创立,同样在2月,陈独秀开始在武昌宣讲“社会改造方法和信仰”,并提出了“新教育”的必要性。
之后的历史潮流便大势已见了。孔德成选择追随“蒋家王朝”,他在南京宣誓时,只有十五岁。年轻的孔德成或许看不到历史的潮流,可即便他看到了,也没有其它的选择。
而战争结束时,孔德成二十五岁,正是大有所为的年纪,然而中国的战争依然继续。1949年,他告别了“他的中国”,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。可孔德成不知道,中国早已不再是他的。他更不会知道,台湾也不属于他。

困于台湾的蒋介石依然以“中华正统”自恃,扶持孔德成做了“政府资要”这个虚职。1954年,他进入了台湾大学,做起了中文系教授。
可他能传授什么呢?只有曾经在“五四运动”中被否定的“孔家家训”。于是,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是如何的扭曲的。她先是否定了一切,之后又承认了一切。
很快到了1966年。在大陆,一场悲剧开始了。在台湾,一场闹剧正轰轰烈烈。孔德成找到了孙科——也就是孙中山的长子——向蒋介石提出了要创立所谓“复兴节”的提议,“复兴”的自然是“中华文化”。蒋介石批准了。
十年之后,中国大陆的悲剧落幕,而孔德成也终于看清了政治的荒谬——虽然一生追随蒋介石,但是已经回天乏力了,这最后一代衍圣公半生换来的只是“明哲保身”,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已。

2008年11月20日,孔德成因肺炎并发症昏迷,住进台北慈济医院。一个星期之后,他死了。如今,孔家后裔多在海外,并不在大陆或者台湾。
有时,历史的复位——正如她曾经的偏离,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。今日的台湾逐渐抛弃了“中华文化”,只留下“正统”一个名号的笑柄。
无论是“孔家”还是“蒋家”,都已经远离了中心地位,反观大陆,国学复兴,“孔家经典”逐渐回到了教育的中心,成为了中华文化的“新教育”。
四、章嘉呼图克图的生与死
孔德成逝世的佛教慈济医院和章嘉呼图克图并没有过多的关联。在孔德成逝世前的半个世纪,章嘉呼图克图早已经作古。这位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中国青海、西藏,华北和东北地区都有着众多的信徒。

章嘉呼图克图生于光绪十六年,三岁时被认定为第十八世活佛的转世,七岁时出家,八岁时被封为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。章嘉一生经历清朝、北洋军阀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,且都担任历朝历代的国师,不仅在民间,还在政界有着极高的威望。
中华民国成立两年后,蒙古在外部势力下试图“独立”。章嘉呼图克图致信蒙古各界,劝说其放弃“独立”。北伐战争结束之后,南京政府遵照孙中山的遗愿,册封章嘉呼图克图为“净觉辅教大师”。
二战之后,章嘉呼图克图进入“南京中央政府”,担任政府委员一职,面对日军威胁和利诱不为所动,从事爱国宗教活动,宣扬中国统一理念,著书立说,讲经传法, 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赞颂。
章嘉呼图克图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同时得到了官方认可。1948年,章嘉呼图克图跟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。章嘉呼图克图一生信仰不曾动摇,而他的政治主张比起台湾省政府,更接近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。

站在历史的高度,章嘉呼图克图的确为人民的解放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做出了一份贡献。他也不愧孙中山留下的一句“净觉辅教大师”。
在章嘉呼图克图过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,他在中国台湾依然是众多民众的精神领袖,而在中国大陆,却藏寺也逃过了十年动荡的摧毁,并在2006年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”。
生前,章嘉呼图克图在讲经传法时被问到,如何才能得道?
他说,看得破,放得下。
随后有人问,如何才能做到看破和放下?
他说,布施。
1957年3月4日,章嘉呼图克图在台湾圆寂,终年六十七岁。
“呼图克图”是蒙古语,意为“生死自在”。
五、张大千的离与合
也是在1957年,张大千眼病复发,他推迟了画展活动,回家养病,但却并未停止绘画。

张大千和佛教的渊源很深,他初到台湾的第一年就前往印度新德里临摹了阿坚塔佛窟,而早在1944年,张大千就已经完成了对敦煌壁画的临摹。
这些画作先后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展出,也成为了中国在二战时期的一份安定——张大千正是如此。无论是在南京、在重庆,还是内战之后前往台湾,他所追求的只是“安定”,哪里能给他作画的安定,哪里就是他的“家园”。
张大千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。张大千的原名叫“正权”。政权,政权……但是,名字中带着一个“权”字的张大千却是一生不问“权”和“利”,他只要画画,他只要安定的自由。

张大千对安定的渴望或许和他二十岁时的一段经历有关——这一年的四川,匪帮肆虐,张大千竟然被匪帮劫持。匪帮领袖看张大千画得一手好画,让他做了自己的师爷。匪帮匿迹,张大千重获自由,之后去了日本留学。
回国之后,张大千便担任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。但是,张大千在大学感到苦闷,觉得教书误事——这一点和钱钟书对上学的态度一样——不久之后,他就辞职了。
他拎起行囊去了青城山的清宫临摹宋代和元代的古迹,这一年张大千三十五岁。从此,张大千就没有停止过“临摹古迹”的脚步,而他的脚步也遍布了中国大地。
为了追求“安定”,他在1951年去了南美洲。那是一片广袤且自由的土地,张大千想要的“安定”便是从这自由中来。然而,在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中国。
今年之后,在巴西的一片一百五十亩土地上,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国式园林建成了,张大千将其命名为“八德园”。而此时,五十一的张大千的名字中早已不见了“权”字,他有了另一个名字——“下里巴人”。

1977年,已经七十八岁高龄的张大千愈加思念祖国。他和夫人舍弃了在巴西的一百五十亩土地,回到了中国台湾。他为自己建立了人生最后的居所,将其命名为“摩耶精舍”,同样的中国式园林,同样的对中华文明的不舍,屋后是张大千精心栽种的梅树。
1981年,张大千寄出了最后一封信,是寄给大陆旧友的。他在信中说出了压在他心头半个世纪,或许也是追赶着他“浪迹世界”、寻求“安定的自由”的一句话:世乱如此,会晤无期,奈何奈何!
1983年4月2日,一代大师张大千在台北仙逝。他的遗体埋在了梅树下。
而此时,傅斯年已经过世五十八年,章嘉呼图克图逝世五十一年,二十五年之后,孔德成也过世了。

而在五十九年之前,曾经带着这些“大师们”离开大陆,前往台湾,此生再未回家的那个人也已经过世三十三年了,他的儿子也在他死后十三年逝世了,蒋家王朝宣告陨落。
这真的应验了张大千那句话啊,在这样的乱世中,谁与谁还能相见呢?奈何啊奈何啊……
六、“大师们”的得与失
国、内外学者说“中国历史五千年,但真正的历史却很短”,是有道理的。纵观中华文明上、下五千年,动荡多,但是变革少,大部分时间只是历史无聊的重复。
在中国,甲午战争击碎了国人天真的迷梦,也让一些有志之士思考起国家的未来。这些人有军人、有政客,也有学者。政客打着自己的小算盘,军人要么听命于政客,要么推翻政客,只有学者——这些如今被成为“大师”的人——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道德。

这些人有着各自的立场,有着各自的信仰,也有着自己的倔强。他们都曾经是、或者现在依然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和文化中的代表人物。他们中的一些人顺应了历史的进程,另一些人则固守着已经过世的伦理和价值系统,幻想着凭借一己之力强撑时代的巨轮,最终被时代抛下,被人民遗忘,只有当我们翻开那本叫做“时代”的大书时,才能在一个注脚中找到他们的名字。
当然,他们中有些人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,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认可,但也有些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一意孤行,他们或许不知道天空已经换了颜色,或者被那颜色迷惑。
而在这些“大师们”中,有些人成功了,将自己所信奉的发扬光大,而有些人失败了,眼看着自己所信奉的被人民摒弃、甚至否定,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们才猛然惊醒,原来自己一生的坚持终究不过是徒劳。
只有坚守自己的信仰和道德的同时,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,得到人民认可的学者,才能真正走进人心,成就学问,成为大师。
内容来源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,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230890.com/zhan/121810.html